深秋的洛阳城,寒鸦点点,枯叶在宫墙间打着旋儿。董卓的大军列阵于城外,甲胄在阴沉的天光下泛着冷光。中军帐内,董卓正对着一道诏书皱眉——天子诏令他率军进京“清君侧”,可这诏书背后的刀光剑影,谁又能真正看清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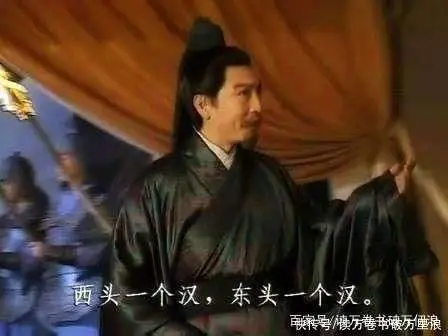
“将军,何进与袁绍等外戚已磨刀霍霍,只待我军入城便一网打尽。诏书虽为征召,实则暗藏杀机。”帐中一人,青衫磊落,目光如炬,正是李儒。他略一停顿,看向董卓,“何不先遣能言之士快马加鞭,上表奏明我军‘奉旨讨贼,乃为大义’?如此名正言顺,方能稳住人心,破其诡计。”
董卓闻言,浓眉一挑,抚掌大笑:“妙啊!先生真乃我军智囊!”当即依计行事。洛阳城中,何进果然中计,以为董卓大军尚远,贸然下令诛杀宦官。一时间,宫闱之内血光冲天,宦官与外戚两败俱伤,汉室根基就此动摇。李儒立于军帐之外,望着洛阳城内腾起的烟尘,嘴角勾起一抹难以察觉的弧度——这盘棋,从他开口的那一刻,便已悄然改写。
董卓入洛阳后,权倾朝野,废立之事便提上日程。温明殿内,气氛凝重。司徒丁原怒目而视,袁绍等士族代表更是厉声反对。董卓按剑而起,正欲发作,李儒却上前一步,躬身道:“相国息怒。废立之事,关乎国本,不可不慎。然若迟疑不决,恐生肘腋之变。不若暂缓时日,待时机成熟,再行公论不迟。”一番话,看似调和,实则麻痹众人,为董卓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
待丁原、袁绍等人稍有松懈,李儒便在董卓耳边低语:“今夜月黑风高,正是动手良机。”当夜,董卓党羽李肃诱使吕布杀丁原、献赤兔,董卓趁机将少帝刘辩、陈留王刘协等一并“请”至殿上。烛火摇曳,映着少帝惊恐的脸庞。李儒面无表情,捧上一杯鸩酒,声音冰冷:“陛下,喝了这杯酒,也好去地下做个逍遥天子。”刘辩颤抖着饮下,旋即七窍流血。李儒又瞥了一眼吓得瑟瑟发抖的陈留王,对左右道:“此子亦不可留。”一条无辜的生命,就此消逝于权谋的漩涡。
董卓的暴行,激起了天下诸侯的公愤。十八路诸侯联军浩浩荡荡杀奔洛阳。董卓连战连败,惶惶不可终日。一日,李儒急步走入中军大帐,神色凝重:“将军,我军新败,士卒疲惫,洛阳已不可守。为今之计,唯有挟天子西迁长安,方可徐图缓进。”

董卓面露难色:“迁都劳民伤财,恐失民心……”
“将军!”李儒打断道,“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!若困守洛阳,一旦被联军围困,玉石俱焚,悔之晚矣!迁都长安,可控关中险要,更有秦川八百里沃野,足可支撑长远。”他顿了顿,眼中闪过一丝狠厉,“至于洛阳……一把火烧了便是!那些不肯顺从的富户、士族,正好借此机会‘清除’干净!”
董卓被说动了。一声令下,洛阳城顿时成了人间炼狱。无数宫殿楼宇在烈火中化为焦土,繁华的都市只剩下断壁残垣。数万无辜百姓被屠戮,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。李傕、郭汜的士兵如同豺狼,驱赶着幸存的百姓,哭嚎声、惨叫声响彻云霄。昔日繁华的洛阳,转瞬间成了阿鼻地狱。
董卓一行仓皇西逃,行至荥阳,方稍喘口气。李儒却不敢大意,他深知曹操乃心腹大患,此番追击,来者不善。他悄声对董卓道:“丞相新弃洛阳,西凉军士气未稳,恐有追兵。可令徐荣将军率部在荥阳城外设下埋伏,以逸待劳,定能重创曹军。”
果不出李儒所料。曹操不听劝阻,亲率轻骑追击。行至荥阳汴水,一声炮响,伏兵四起!徐荣、李傕、郭汜三路兵马杀到,将曹军团团围住。曹操左冲右突,险象环生,坐骑中箭倒地,自身也身中数枪,几乎殒命。危难之际,曹洪及时赶到,大喝一声:“天下可无洪,不可无公!”将自己的战马让与曹操,自己徒步断后,浴血奋战,方才杀出重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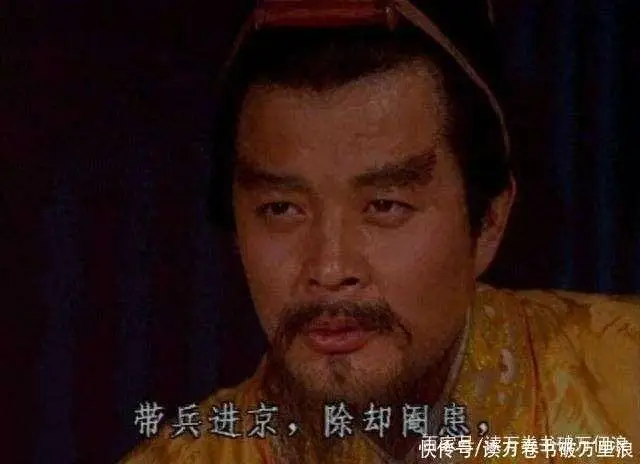
李儒立于高处,望着狼狈逃窜的曹操,眼神复杂。他知道,今日一役,虽未能取曹操性命,却也大大挫伤了联军的锐气。只是,他未曾料到,自己这一步棋,竟为日后埋下了如此多的变数。
夕阳西下,为荥阳城头镀上了一层凄艳的金辉。李儒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仿佛一个穿梭于乱世棋局中的幽灵。他的一言,挑起了外戚与宦官的死斗;他再言,终结了大汉四百年的帝祚;他三言,险些断送了未来曹魏的基业。这个在《三国演义》中着墨不多的谋士,用他的智慧与狠辣,在东汉末年那幅波澜壮阔又腥风血雨的历史画卷上,留下了一道深刻而独特的印记。他或许不是最耀眼的那颗星,却是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幕后推手,一个以智谋与冷酷,亲手搅动天下风云的“影子帝王师”。